奧地利影委會KARIN SCHIEFER:《人類之後》比較異於傳統紀錄片的一點是,它將它的拍攝主體視為某種不再存在的東西。這部片展現了一種未來視野的可能性。你的作品至今大多關注的「人類」,在這裏不復存在了。是什麼讓你採用這個激進的切入點?
《人類之後》導演NIKOLAUS GEYRHALTER:首先,我不會真的將《人類之後》描述為一部紀錄片。這是一部(有虛構成分的)電影。是電影工業與影展需要將影片分類。在這情況下,我覺得《人類之後》只有部分符合這種分類規則。這部片或許更貼近於紀錄片而非有主軸的電影。但我之所以認為《人類之後》是個十分虛構出來的製作,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介入了很多,也改變了很多。那些樹啊、建築物,甚至是風,都幾乎成為為我存在的演員。我從來無意要描繪出一個紀錄片底下的真實狀態。對我而言,這部片是比較貼近虛構電影的視角。它的紀錄層面其實是在於拍攝的建物、地貌,在今天都還找得到。或者至少在他們被拆毀之前可以。
KARIN SCHIEFER:在諸如《我們的每日麵包》和《這幾年》幾部片中,你呈現了機械在工作生活中扮演越來越主宰的地位,同時,人類面向的工作型態就被排除了。《人類之後》的關注主體是世界在人類之後、機械之後呈現的狀態。這種狀態是怎麼被描述出來的?
NIKOLAUS GEYRHALTER:這是閱讀這部片唯一可能的方式,當然啦,這是被設計成這樣好讓詮釋得以可能的。但我不想以化約的方式把此片視為一個後啟示錄的單一視閾,因為即使它有種人類反省視野的可能,對我而言它還是一部強烈在勾勒「這一刻」的電影。藉由這種激烈的缺席,所有的人們是更加現存於此的。某方面而言,這是部關於人的電影,即使人們不在裡面。
KARIN SCHIEFER:就這角度來說,《人類之後》是你虛構氣息最重的片,因為每個被拋棄的、淡出的、腐朽中的場景在凋蔽之中都在索求著一段過去的故事。但同時它又被完完全全地遺留下來,讓每個觀者激盪出他/她自己的猜想。
NIKOLAUS GEYRHALTER:這就是《人類之後》該有的樣子。
KARIN SCHIEFER:這部片的片名取自人作為物種的自然定名,在片中也似乎預示著它的絕跡。你選用這個片名的動機是什麼?
NIKOLAUS GEYRHALTER:一直以來我們都以《某個時候》作為工作用的標題名,不過我們也知道必須找到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因為《某個時候》太清楚地預期了一種「未來人們不再存在」的視野。我希望留下更開放的詮釋空間,而不是去暗示某個觀看此片的唯一方式。我越來越對人類本身,以及我們現在為什麼身處在這裡、我們又會遺留下什麼東西的問題感興趣。確實片中呈現了一種對環境有所責任的觀點,這也是為什麼把「人」放進片名是很重要的。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去找到對的字眼。我想,把生物術語「人類」在此做個轉變是好的,精確來說是因為在這個脈絡下你真的不會預期到人會在片中缺席。且它又有關乎考古學與歷史的聯繫。
KARIN SCHIEFER:這些意象通常都暗示了某個地點突然間被參與其中的所有人棄置,而這也引起了關於那裡「發生了什麼事」的問題。研究團隊在尋覓適合拍攝地點時有什麼標準嗎?
NIKOLAUS GEYRHALTER:研究內容變得越來越特定。一開始我們只是找一些荒涼的地方,那種被拋棄式的荒涼。像這樣的地點很好找到,但我們發現它很快就變得很平庸。我們需要的場景是需要有故事連結的,是那種你可以看出它本來發生了什麼事的地方。一個空無的工廠、被摧毀的房屋——就並不特別有趣。重要的是一個地方它擁有些故事,卻又不必然使你感到同情。我們開始著重在尋找一些無需解釋就能判讀出其歷史的場景,這些場景光出於它們的那些維度就已足夠使人印象深刻,又或者它們因為被自然重述,而進展成更好的狀態。在我們剪輯時,很快就發現到這部片顯然需要不斷往某種新層面推進。最重要的一點是找到符合我們前提預設的場景:我們想創造出一個對向於人類的關鍵性樣貌。
KARIN SCHIEFER:你可以很快認出這些郊區廢墟中的基礎建設跟機構。
NIKOLAUS GEYRHALTER:對,重點擺在人類的系統,以及人們如何自己組織起來的問題上。而且我們是有意識地決定不去呈現任何私人空間。很自然,我們做出各種選擇而讓指認事物很簡單。有很多場景並不蘊含那種可能性,所以意象與場景能夠自己說出過去的故事是很重要的。我們有些以切換鏡頭來對應順序的段落,實際上它們如何被拍攝則並不重要。然後有些特別的場景可被指認為連結的建物,或甚至可能像個島嶼。這些例子是為了一個很不同的目的:呈現出一種完整解構的地理光譜。
KARIN SCHIEFER:意象與空間可被視為你致力於影片的兩大支柱。你似乎能以排除這兩者的方式,專注於尋找一個以純粹形式拍攝觸手可及事物的挑戰。
NIKOLAUS GEYRHALTER:這不是我第一部僅用影像建立起敘事的片。這只是第一次影像中沒有任何人的參與。《人類之後》或許是我拍過的所有片中最「攝影」的。影像對我而言一直很重要,甚至還在增長,所以在這部片中它躍居最重要的位置。拍攝《人類之後》是連串處理觸手可及事物的過程——不過我們只操作我們覺得有必要性的可及周遭。比方說,我們製造風。在剪輯過程到了某個點時,內部的運動太少這件事變得很明顯,也不可能單單藉由加入聲響去處理這種毫無生機的生活。有時我們也調整光線,通常我們用數位輔助來讓物件更加完美,並能維持住關注。我們希望連一丁點人為噪音都不要被聽見,所以我們在錄音上很難完全用原場收的環境音。現在我們聽到的聲響都是以可得的素材為了每個影像仔細製作的。大量的聲音為了這目的被特別錄製下來。
KARIN SCHIEFER:你為了拍攝多大程度地跑遍了世界?
NIKOLAUS GEYRHALTER:我們在歐洲和美國進行了很多拍攝。我們在阿根廷找到一個曾被鹽湖淹沒的地方,然後湖水又再度沉下去了,留下一片被鹽覆蓋而白茫茫的地景。我們剛好在對的時間去到那裡,那時還沒留下任何可見的足跡,天空也十分完美。我們在某個下午捕捉的場景在影片中成了一個五分鐘的片段。我們也在日本拍攝了很多,部分原因是要拍電影末尾被遺棄的島嶼,也出於福島核災的事件。影片開始於保加利亞紀念碑上的馬賽克,然後有一系列從福島拍攝的影像。你大概好長一段時間不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殘局還沒有很大程度的進展。我們是在距離核電站大約四公里的地方拍的。
KARIN SCHIEFER:在一個須控制外於語言與人的片中,節奏變得更加重要。這些系列長度的轉變是拍攝時就有的直覺,還是到了剪輯時才決定的部分?
NIKOLAUS GEYRHALTER:我們在初期都同意影像節奏會是緩慢的,每個場景都會被拍攝約莫一分鐘。在影片要結尾時減到剩半分鐘。一開始剪輯時,我們用主題來安排影像來測試弧形有沒有在運作,並沒有太對節奏擔心。然後,在版本的基礎上,Michael Palm開始處理這序列的節奏。所以那些相較之下被呈現更久的影像,都是花了更長時間去消化,也是你會想看得更久、或是因為風的緣故出現了不同節奏的。這是第一次Michael Palm剪輯我的片子。當我在攝影一些我自己基本的原則時,我會拍每一鏡,而剪輯師擁有很大量的自由。目的就是要找到每個影像最正確的韻律,就像對勁的呼吸速度以及合適的脈絡。這不是我的強項,我很高興有人幫我接手。這確實是部需要緩慢的影像節奏才對勁的片子,從第一分鐘起就很明顯是這樣。觀眾從最開始就會知道要期待甚麼。
KARIN SCHIEFER:這部沒有語言或人物的影片,需要很強的聲音元素。你與Peter Kutin合作,聲音上的工作包涵了什麼?
NIKOLAUS GEYRHALTER:我實在不知道誰能比Peter Kutin做得更好,因為我不知道哪個人能把聲音玩到這種程度。Peter Kutin通常為我處理聲音設計,不過《人類之後》達到了聲音設計的新層次,因為實際上所有事物都有開放的解釋空間。除了幾個少數的場景以外,Peter在剪輯房中臨場賦予沈默的影像充滿氣氛的聲音。我們很仔細地分析了你在各種可能中會聽見的聲音:一張紙在風中的聲音、一片金屬的刺叫聲、一隻鳥……等等,就像在為默片配音一樣。這是個花了好幾年的鉅大工程,直到最後都還是很令人興奮。
KARIN SCHIEFER:你總共花了多久時間製作《人類之後》?
NIKOLAUS GEYRHALTER:一定有四年了吧!不是毫不間斷,但我們一直有在持續回頭製作。事物持續在變,我們必須放棄某些在拍攝前已經被拆掉的場景,並加入其他的替代。一次次,我們轉向某處開始拍攝,遺留下來的除了廢墟外什麼也沒有。這通常發生得很快:你在片中能看見的雷達天線在拍完後就消失了。有時我們實在很幸運。當我們在拍一些屠宰場時,建物遠處的盡頭已經開始被拆除。我們很常在網路上找到想拍的地點然後發現它們根本就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來說,日本的島嶼是個古老的、不在有利可圖的礦業島嶼。很多城市中孤立的建築物不僅並不能持續許久,或是由於他們是私有財也不能拍。然而研究在背後一直持續,而且總是還有一堆事可以做。這部片並不在任何自然意義上有它終結的時候,你可以繼續永遠地拍下去。
2016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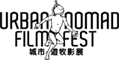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