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者:《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導演曾涵生
大雨敲打著鐵皮車棚,棚內腳踏車東歪西倒,火車月台掩映在亂草之中——棄置的單車與荒廢的鐵軌,揭開了《人類之後》九十分鐘無人風景的序幕。交通工具的鋼鐵材質,看似笨重卻弔詭的承載著速度感,歷來一再化身為現代性最貼切的視覺隱喻。例如早在廿世紀初期,《柏林:城市交響曲》便透過疾馳的火車、交錯的鐵軌,給出了都市現代性經驗的視覺化表述。這份集結各式現代發明而創造出來的視覺驚奇,乘著資本主義文明的高浪,在1980年代《機械生活》宛如巨大雕塑的巨無霸客機與幾何狀高速公路結構體中,登峰造極。
如果說《柏林:城市交響曲》在興奮、樂觀的旋律中,陶醉於渦輪、櫥窗、電車等等新奇的人工造像,半個世紀後,《機械生活》已經在其科技文明的禮讚裡,混雜了爆破、墜毀、戰火,提示了警覺與不安。又過了三十年,《人類之後》最終被譜成一篇悲愴的廢墟交響曲:現代性烏托邦已然幻滅,浩劫奇觀取代了造物奇觀。從這一層意義來看,《人類之後》或可視為一則帶有生態意識的影像寓言。
學者魯曉鵬最近在一篇論文中,梳理生態電影批評的理論源流。文中指出,生態電影(ecocinema)多採取長拍、緩慢、靜止等美學手法,積極喚起觀眾的環境意識。這種電影風格,彷彿中國傳統醫療的證候學,在望、聞、問、切中考掘癥狀與病候,從而給出診斷與處方。《人類之後》於是成為一種電影病候學,攤開一切現代文明毀壞、崩裂、腐蝕的視覺證據,敦促觀眾自己給出一個診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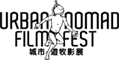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