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Ning Kung
午夜,來到練團室「肥頭」,甫走下佈滿塗鴉與海報的樓梯,就聽見被牆壁過濾變得有些失真的斷續旋律。樂聲漸歇,傷心欲絕的團員們伴隨一股酒氣走了出來,目光交接的時候,這夥人嘴角的笑容有些保留。除了不克出席的鍵盤手,傷心欲絕的其餘五位團員參與本訪談。樂團成員買好更多的啤酒與菸,逐一卡進了練團室的沙發,他們的表情在煙霧中逐漸鮮活起來,而剛才隔著牆壁聽見的樂音彷彿也變得真實立體。
我們就是我們音樂呈現出來的樣態

2008年開始活動的傷心欲絕主要由主唱許正泰與吉他手劉暐包辦寫歌,節奏明快的旋律以及簡單直白的歌詞反映了他們的人生。這樣的反映並非單向投射,而是交互共構。許正泰表示,從二十五、六歲開始,人生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這個樂團,很多事情都依此做決定,樂團的活動與興衰也主導了他的生活起落。
其他團員在傷心欲絕則擔任樂手的角色。金剛笑說,「我們算是坐享其成,他們寫好了就丟給我彈吉他,所以包袱沒有他們重」。他也解釋了許正泰及劉暐作品的差異,認為劉的音樂結構非常簡單,較在意細節;許的作品想表現的相對不明確,非常複雜。「身為一個吉他手,面對這兩的人的創作要用完全不同的心態,用兩種想法、兩套作業方式,來處理一個團的音樂」。貝斯手阿祖補充,如果有哪段旋律怪怪的,其他人也會提出建議修改,但整體來說「歌曲滿直接的,滿好上手」。
談到歌詞題材與團名的緣由,許正泰解釋「因為我們比較悲觀」。此時金剛插話「劉暐的歌極度悲觀,超悲觀」,他笑得一臉開心;咧開帶著大鬍子的嘴角把「超」字拖成一個歡樂的長音。劉暐沒有否認,淡淡地補充,「探索自己內心的這一面是比較有趣的」。
傷心欲絕計劃在六月推出新專輯並展開巡迴。新專輯最明顯的變化就是歌的長度變長,內容也比過去複雜。許正泰表示因為年紀和生活的變化,作品型態也有相應的呈現,「(過去)寫很多關於喝酒的歌,是因為當時相信這是生活的一種救贖,但現在那已經不是我生活的樣子了,還是有別的想說,要是再硬寫那樣的歌也覺得噁心,要騙誰啊」。關於新專輯的內容,他半開玩笑地說是「人生過程的偉大發現」,又懶懶地接了一句「但其實好像也是什麼都沒有發現」。
關於樂風,團員們在定位上有不同看法,對於傷心欲絕是否是一個龐克樂團,他們在內容、曲式以及他們所喜愛的其他樂團影響上都有不同分析。許正泰表示「就是一個搖滾團,以內容來說,可以說是比較吵的民謠團」。金剛反駁「我覺得他嘴硬啦,就是龐克團」,又開了一瓶啤酒之後,他卻悻悻地說身為90年代的小孩,長大在資本主義消費至上的社會裡,有電動和很多玩具可以玩,「怎麼可能龐克的起來」。
可以確定的是,傷心欲絕受到龐克音樂很大的影響。劉暐說「因為小的時候就聽這些音樂,我們拿這些東西來做我們自己的音樂,受的影響當然很多」。提到喜愛的英美龐克樂團如Ramones, clash, against me等等,他們笑得開心,聊著這些樂團近況並順著說了些荒謬的笑話。劉暐總結,以曲風歸納,當然可以說傷心欲絕是龐克團。但精神層面來說,龐克團應該反叛、抗議一些什麼;傷心欲絕則沒有一個反抗的對象,「我們就唱一些生活上的小東西,要說我們自己是龐克樂團,我們自己也不確定」。許正泰補充,「不能說你很膽小,就代表你是右派。龐克樂團至少會覺得自己是在為了某個偉大理念付出,但我們沒有。」
只有特別的事情才會讓你記得一場表演
訪談中傷心欲絕分享了他們對表演的看法以及多場演出過程中他們最難忘的幾次體驗。提起過去的表演,無論好的壞的,他們講起來都眉飛色舞,大概是整晚最開心的一段對話。
談到演出,劉暐表示,「我活的不是很開心,但表演的時候很開心」,又接著解釋「我講一個故事給別人聽,然後他們的反應很好,我就很開心啊」。他比劃出一群不存在於現場的觀眾,對他們說「嘿你聽懂了嘛」,才又回到了真實存在的我們,總結道,「我就覺得很爽」。
許正泰則分析了自己看法的轉變,「以前覺得跳到台下去來觀眾互動滿開心的,但現在覺得觀眾也沒必要這樣勉強;沒必要硬要人家很開心。我現在比較想要好好做一個表演,不一定要很激烈」。他接著說「精彩的表演,觀眾會看得目不暇給,真的有感覺得時候,就會跳舞」,說這段話時許正泰的表情篤定而柔和,語速略緩,與台上那種彷彿要吐了似的把歌詞和情緒全部傾瀉的樣子一點都不一樣。
阿祖對表演的看法相對單純,「表演不出錯就很開心,看到別人出錯就很爽」。大家都笑了,團員們互相開起關於對方出錯的小玩笑。「只有特別的事情才會讓你記得一場表演」,金剛說起了傷心欲絕表演過程中遇到的種種神秘體驗。

去中國表演都是神秘體驗:
樂團去中國參加音樂祭,因為主辦方出包,不只讓他們錯住到陳珊妮的飯店房間,還導致金剛和阿祖沒有趕上回台灣的飛機。被多留在中國一天的他們決定回去參加音樂祭,並與當地認識的人隨機地決定要去看在音樂祭偷錢包的小偷被打。「那個小偷被打得超慘的欸!最後還有人說『不要污辱搖滾,把他交給警察!』」金剛一人模仿兩組人馬的聲音、姿態,表演得非常開心。
傷心欲絕最好的表演之一:
樂團在中國青島某度假村唱開幕典禮,「台下都是解放軍,被規定要坐著」許正泰說到這裡聲音裡已經帶著笑。唱結束以後熱情的軍官堅決要請樂團吃飯,許正泰接著說「我們還被尾…護衛(金剛:尾隨啦/阿祖:監視!)回飯店」。在團員對於某個動詞爭論不休的同時劉暐卻正色說道「我覺得是傷心欲絕最好的表演之一!唱完之後你可以看到台下的反應,一群很拘謹的人有辦法站起來替你歡呼,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非常滿意他們讓那些被規定要坐著的人站起來了。
發生在一瞬間:
大概是他們最喜歡的一個故事,簡潔明瞭直接而且很短,和他們的歌有點類似。團員爭先恐後地說,一起把故事拼湊起來:一次沒有太多觀眾的演出後,不太開心的一群人坐在表演場外發呆。就在聽到幾聲「不好意思,借過噢」後,旁邊的鹽酥雞攤就被打了,打人的打完就跑了。「兩台房車停下來,六、七個人,說完借過就打,兵兵乓乓超爽!」金剛難掩興奮地說。阿祖強調「真的很一瞬間的事,我那時候落枕,想看還來不及轉頭就結束了」。過程不到20秒,瞬間讓他們變成非常開心的一群人。
表演完哭了:
某音樂祭因為表演排得太晚,上台前已經喝得太醉。「金剛在台上沒有一個和弦按對,下台被團員檢討就哭了」,許正泰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個感覺當下是個災難的故事。「但沒有一個和弦按對台下也不是很在乎,你看台下也喝得多醉!」金剛試圖說點什麼,並且非常堅持「我平常都是彈對的」。
誠實、真摯並且毫不保留,樂團說著他們的故事又開了幾瓶啤酒,搭配各種音效、手勢,彷彿回到那些場景。說到激動處大家拍手、大笑,並搶著補上更多細節,這個晚上好似可以一直這樣延伸下去。
來來去去的事情超複雜,但在人海中他們留下來了

他們的音樂寫他們的生活,歌詞、節奏相對簡單直接。但這個樂團是複雜的,複雜的程度讓許正泰在兩分鐘內說出了「我們感情很差」、「我們感情很好」、「我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傷心欲絕成立至今經歷數次團員變化甚至休團,半數以上成員目前同時參與其他的樂團,且選擇把自己想表達的在其他的樂團呈現。劉暐在新專輯中不再寫詞,他寫的詞都在他的另一個樂團“勝利一族”;「自己想要說的話就不會在這個團說啦」,金剛附和。
作為傷心欲絕的主要創作者,許正泰和劉暐有些歌會一起寫。然而談到共同創作的經驗,劉暐飛快又簡潔的回了「盡量不要」,而許正泰則解釋道「因為我們兩個太容易吵架了,沒有一起合作的話當然是可以當很好的朋友,但是合作的話就很容易會有衝突」。劉暐曾經離開傷心欲絕,關於為什麼又決定繼續和大家一起玩團,他認為過去的努力讓他不能輕易放棄,「一起合作這麼多年了,很像一群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只能跟著那個籃子走了啊。」他的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憂,但一旁的團員們舉了幾個籃子與雞蛋的比喻,自得其樂起來。
這些人事聚散逐年畫出一個龐大複雜的網絡,許多關係可以追朔到學生時代,許正泰和劉暐甚至是十幾歲就認識的鄰居。而他們全都是朋友,老朋友。關於到底是感情差還是好,許正泰花了一段時間總結,「雖然感情不好但是有默契。感情不好不是不喜歡這個人,只是一起合作上會有很多摩擦。這樣也可以說感情算很好」。一路都參與傷心欲絕的阿祖補充,就因為是老朋友,「認識太久了,會有成見,有些話沒辦法直接說出口」。很簡單的事情,誰都會在生命裡碰到類似的情境,但他們能夠坐在一起說出這些話來,那種坦率的樣子並不是一般生活裡常見的。那種坦率也反映在他們的歌裡,彷彿某種心理治療般,誠實地替聽眾把大家的心裡話都說出來了。
正規訪談結束後,樂團在附近便利商店門口落腳,聊著與採訪相關或不相關的事。我又問了一次為什麼他們不寫開心的歌,甚至連團名都要傷心欲絕。許正泰說因為他們的人生就是這樣,長成了怎樣的人就寫怎樣的歌,隨即又反駁說他們有他們的小幽默。「傷心欲絕這四個字應該是這樣念的」,許正泰就這樣演繹了起來。他說出團名的時候聲音帶笑,比較戲謔的那種,又在四個字後面加了長長長長的一串人工笑聲,這樣的表演引的在場的我們都笑了,比較真摯的那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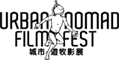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