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策展人David Frazier、《台灣政治重金屬》導演Marco Wilms、立法委員/閃靈樂團主唱Freddy 林昶佐
David:Freddy, 我看到前天自由時報有關於這部紀錄片的報導,上面提到你在看到電影裡的某些片段時有哭,想請問讓你哭泣的是哪個部分?
Freddy:我去見達賴喇嘛的時候,身邊沒有任何人,包括同行的一整群朋友也沒人知道我太太Doris懷孕,所以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當我跟達賴喇嘛講完正事,正要跟他分享這件事時,我沒來由升起一股情緒,對我來講那是很複雜的感覺。
從決定參選、組成政黨造成家裡的人很多困擾,這個困擾就像有了一個小孩子但是不能告訴任何人,因為你很怕記者跑來報導等等。在座的一些朋友知道這件事後來變成是我跟Doris先承認,原因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人在偷拍。就是這種心情。當你做了一個決定,那個決定造成令很多親密的人感到痛苦與困擾,所以那時我跟達賴喇嘛坦承-那個事實上第一次跟外面人講的那種心情,令我看到電影覺得很感動。
我身為立法委員也兩年了,再頭看當初做的這些決定以及努力,也是滿感動的,因為自己在立法院裡,每天都會被很多瑣事把自己的耐心與熱情磨掉,真的是好險有這部電影,讓我看了覺得我還在這個自己決定的軌道上面。
Marco:看到Freddy見達賴喇嘛這一段的時候我也覺得非常感動,即便Freddy說:「我太激動太感動,拜託這段不要拍進去」,但我還是拍了。
Freddy:我回應一下Marco講的,老實說,就是他也知道我其實一開始是蠻抗拒拍這個紀錄片,我一開始以為就只是一般的電視台訪問,結果真的拍下去以後他什麼都要跟,我就跟他說,我是立委不是演員,但他依舊一直告訴我說,「這個東西很重要,對台灣也很重要,對你這前兩年也很重要。」只好相信他了。老實說,在座有些人應該有看到我跟他吵架,我曾經對他很生氣地說,「不要再拍了,你什麼東西都想跟,我真的無法忍受!中間有好幾段我也跟他說我不想放,但最後也是他的堅持說服了我,只能說他很有……拍紀錄片的體質。
後來他叫我去看初剪,我也是抱持著一種「怎麼又來了、以為你已經不想弄這個計畫了」的心態,但當我真的看完了,我真的是有點感動,然後也有點改觀,覺得幸好有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
David:你們主要爭論、吵架是在於哪個部分?
Marco:Freddy一開始就在立法院質詢,其實那時候我也沒有任何可以作為正式攝影的文件,其實大家剛剛看到的畫面有一些是Freddy的團隊跟助理用手機拍的,因為那時候Freddy以為我是記者,他說你有什麼問題趕快問一問,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我要跟拍你兩年。」
Freddy:其實在跟拍達賴喇嘛的時候,我就是蠻堅持希望他不要放的,所以就有點不愉快。
後來另外一次是到凱達格蘭大道參加同志大遊行,當時我有上去講話,Marco問他可不可以到後台拍攝,然後就一路跟著我。我記得那應該是我第一次大爆發,我很生氣的跟他講說:「同志遊行的這些主辦單位,所有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不是演員,我也不是演員,我真的沒辦法讓你去拍我的朋友,我也開不了這個口。」,反正那時候我們就在凱達格蘭大道前面吵了一陣子。
Marco:因為Freddy當初要拍這個紀錄片的時候,有個條件是:「不要干擾任何工作的部分,我就讓你跟著我拍」
David:Marco你認為你有沒有捕捉到真正的Freddy?
Marco:我自己也問過Freddy類似的問題,「我真的有拍出你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嗎?」我有拍出來嗎?因為一個搖滾巨星、一個還會在演唱會舞台上焚燒國民黨黨旗的人突然搖身一變,穿白襯衫、像上班族一樣衣冠楚楚,真的是非常大的改變。但對Freddy來講,身為一個搖滾巨星跟立法委員,其實是合一、沒有什麼分別的。
對我來講,我覺得拍紀錄片是一場很有趣的冒險,紀錄片的精髓應該是要去觀察這個人、這個事件真實的樣子,而不是帶有任何批判眼光的。
觀眾:感謝Marco與Freddy雙方的耐心才有辦法成就這部紀錄片,同時台灣也可以藉由這部紀錄片向西方其他國家展現台灣這個國家的存在。我了解一直對抗中國的霸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在西班牙當老師,之前我的學校舉辦台灣文化活動,但也因為舉辦這樣的活動,我們的校長被中國的大使館發政治信函威脅必須取消活動,促使我開始關心台灣政治議題,開始研究台灣歷史,我認為要以非衝突的方式來解決台灣現有困境是件很重要的議題。
Freddy:我覺得這幾年台灣的外交政策或國際的策略都正在改變,而且是往好的方向的改變!但是仍需要台灣人及政府有勇氣去往這個方向走。在過去,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花錢買小國邦交,但是你其實可以看到這兩三年會幫台灣在各個國際場合發聲的都不是邦交國,而是像是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韓國等等,這些國家之所以會幫我們講話,最基本的原因是我們實際上跟這些國家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
我們要把資源用在對的地方,真正加深人民跟人民的關係,這是我覺得我們現在每一個人可以做。在自己的產業上面去思考健康的國際化是怎麼樣,一切才會水到渠成;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已經跟很多重要國家之間的來往很密切了,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都會站出來,我覺得這就不是衝突的方法,是一個有耐心的方式。
觀眾:請問導演,早在太陽花革命之前就有年輕人站出來,以實際行動表態,但你的影片節奏會讓人覺得好像太陽花之後,年輕人才突然開始關心政治議題,所有運動都爆發出來,但現實不是這樣子的。
Marco:某方面來講,這個紀錄片表現的還是從我的觀點來看台灣。在台灣開放、自由民主化之後,舊的結構遺毒與制度還是存在,但《台灣政治重金屬》要考慮到給國際觀眾看,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了解台灣的歷史背景。
Freddy:我剛剛也想了一下Marco的意思,我在看紀錄片也有一個啟發,我覺得他的意思是,他對整個社會的看法有他的觀點,但就影片而言,也有未能完全掌握的部分,就像他沒辦法去控制林昶佐在鏡頭前會是什麼樣子。
David:Marco遇到的問題就是台灣的歷史很複雜,要在有限的電影長度及篇幅解釋給不了解的台灣歷史的外國人聽,可能得作一些取捨。
觀眾:我有兩個問題,導演是因為Freddy才拍攝台灣,還是因為台灣才拍攝Freddy?這是第一個問題,因為這跟你要強調Freddy這個人,還是要強調台灣的民主進程有關。
第二個問題是,導演身為一個德國人,你的國家經歷過納粹還有像是東西德冷戰時期,德國對於轉型正義的過程,我相信也可給台灣參考。你到這裡來拍攝太陽花或是之後的運動,或是像剛剛另外一位前輩提到的,台灣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就一直有很多這類紀錄片工作者或是社會運動在進行,你身為德國人為什麼要選擇台灣或是拍攝這樣的主題?你怎麼看台灣現在的狀況?
Marco:當然是因為Freddy才拍台灣的,其實在德國也沒有一個搖滾巨星可以最後進入國會還當了議員,我想目前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好像也沒有。 我出生在東德,但我其實是反共產主義的,只是說這樣的背景讓我在共產主義的解構方面有比較多的想法。我在片頭一開始就放了Freddy表演的影片,這是用藝術來詮釋歷史的方式,德國觀眾對這個作法應該也會有興趣。
觀眾:其實有很多在台灣定居、想要得到公民權的外國人,但是台灣的移民法其實是很落後的。
Freddy:關於移民法的部分,我必須老實講,在立法院裡對於這種辯論其實是很保守的,你如果去看我們的規範,事實上就算個人融入這個社會,但要拿到任何權利都是困難的。要怎麼辦?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在立法院裡繼續努力;另外一方面,我也認為台灣以一個比我們想像還要快的速度在進步,例如說LGBT的權利,我覺得在五年前沒人會相信,台灣的大法官竟然會說:不能結婚是違憲的。我對台灣年輕人這一代很有信心,控制整個官僚體系的那一代終究會被年輕人慢慢淘汰,所以我是比較樂觀的,這也包括我為什麼會到立法院、為什麼要組新政黨的原因,我覺得年輕人很重要。
至於台灣軟實力是不是失敗了這件事我倒不這麼看,最近全世界都慢慢看到中國的本質,不管澳洲、印度或是很多重要的國家開始重新思考、檢舉中國孔子學運等等,中國跟各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不是讓很多國家開始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覺得有。至於台灣的部分,我也不認為是失敗的,我們跟日本、美國、還有這一兩年跟澳洲的民間交流變得很好,原因都不是因為對方是民主國家、他們也認為我們是民主國家,我認同的是不管是學術、文化,尤其是做生意方面的這些連結很重要,這種連結從我看到的數字跟趨勢,台灣人只有越來越國際化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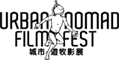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