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一:熱烈迎接神秘客
主持:宜楹
來賓:《湯瑪斯日記》(導演劉維泰+製片焦靜雯)
《歡迎光臨龍岡清真寺》(導演鄭瑋萱+製片馬穎羚)
- Q1主持人:請問《湯瑪斯日記》的導演為甚麼會想以南斯拉夫內戰的背景來拍攝故事?
A1劉導演:我妻子是紐西蘭人,那時我們在紐西蘭認識東歐的克羅埃西亞難民家族,常聽他們分享一些家族逃難的故事,那時就動過念頭想要把故事拍成電影,但紐西蘭當時製作的條件不足,一直到了美國才找到克羅埃西亞第二代和塞爾維亞教堂,兩邊雙方合作才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 Q2主持人:請問《歡迎光臨龍岡清真寺》的導演,據我所知您本身非伊斯蘭教的信徒,請問為何當初會選擇伊斯蘭教信徒的故事來拍攝?
A2鄭導演:這是我大四的畢業製作,因為考慮到製作時間長達一年,想找一個近一點的拍攝地點,自己從小住在龍岡,龍岡清真寺就在我家附近。而這是個很特別的地方,正如片中的一位角色提到,常常經過清真寺卻從來沒機會進去,於是自己想藉著這次畢業製作的機會來了解(龍岡清真寺)。
- Q3觀眾:電影在克羅埃西亞拍攝,請問劉導演拍攝電影前有做甚麼功課來幫助自己了解克羅埃西亞當地的文化或歷史背景嗎?
A3劉導演:之前在某影展中看到一部片《奧瑪的抉擇》,當時就在思考「要拍一個不同國家的題材到底要放進甚麼樣的元素?」。當時把我們想呈現的東西先寫出來,再給克羅埃西亞歷史系的教授去背書,去看這樣一個故事應該會發生在甚麼樣的地方,包括他的電影位置、士兵從屬於哪支部隊,當然還有美術設計的部分。舉例而言,當南斯拉夫這個國家還存在(還未分裂)時,塞爾維亞有一種菸,類似於台灣的長壽菸,而這種東西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他還原,這部分就比較困難。而服裝的部分,我們到了華納兄弟片廠借,發現很多服裝都是過去電影沒有拍攝過的,所以很多東西我們都是從零開始製作。另外我們其實是在美國拍攝,因為克羅埃西亞不講英文,而我們找的演員包括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波士尼亞、甚至俄羅斯人,屬斯拉夫語系,所以學語言會比較快,但若觀眾有仔細留意演職人員名單的話,可以發現有些是後來才配音上去的。我們找的演員是克羅埃西亞的第二代,他們演的是上一代的故事,依著有些逃難未成功者所留下的日記,他們須要靠想像來揣測逃難過程中發生的事。
- Q4觀眾:想請問國光清真寺的製片是如何認識導演的,而在合作的過程中是否有遇到甚麼困難或有趣的事情?
馬製片:我和導演是國中同學,從小就認識。過程中如何製片的?本身是伊斯蘭教徒,沒有做太多功課,就照著我們熟悉的過程製片。
鄭導演:我從小吃素,國小的時候吃素的人都會聚到保健室一起用餐,當時就看到很多像馬製片一樣的人,但我不知道為甚麼他吃素,國中才和馬製片同班,知道他是穆斯林。因為馬製片的關係我才有機會踏入清真寺,一般人雖然可能覺得清真寺很吸引人但可能沒有勇氣走進去,還是感覺到有一種界線,覺得彼此是不太一樣的人,雖然都生活在龍岡。是馬製片帶我進去,認識很多人,發現穆斯林非常熱情、非常好。當初並沒有預設要拍誰,很混沌進去清真寺,是拍完一個(受訪者)說某某是我好朋友你要不要去拍他,接連拍了很多人,最後選了這三位(放入電影)。 - 《湯瑪斯日記》中有兩段吉他音樂,第一段是塞爾維亞人在餐桌上彈奏,感覺想透過音樂來溝通和解的動作;片尾當湯瑪斯走了,塞爾維亞人又若有所思彈了一段曲子,請問在電影音樂的編排上是否有特殊的涵義或是設計理念呢?
《湯瑪斯日記》音樂製作:觀眾其實可以看得到導演的想法:主角想用音樂去和湯瑪斯和好,所以以彈吉他表示善意,而那個吉他彈的旋律其實貫穿了全片,從一開始營區外的鋼琴聲、中間想藉由彈吉他和好,及片尾在這個旋律中又加入一些人聲和一個俄羅斯的樂器。所以整部片是用一個旋律在敘述這個故事。
- Q6湯瑪斯日記音樂製作:想問導演片中關於「納粹人要如何說服士兵去戰爭」及「某某大屠殺」的典故。
劉導演:這場是1990年爆發的克羅埃西亞獨立戰爭,也就是南斯拉夫的內戰。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土地相連,而斯洛維尼亞雖同時宣布獨立,但因為地處南斯拉夫相對邊境的位置,所以衝突沒有那麼大。所以這場戰爭當時爆發的時候,塞爾維亞總統被國際法庭指控對克羅埃西亞人進行屠殺,雖片中這場戰爭是塞爾維亞被控屠殺克羅埃西亞人,但塞爾維亞人也一直諷刺克羅埃西亞人是納粹分子,這是因為一戰時希特勒還是魅力領袖,還未被人知道集中營等事,當時曾經有段歷史,克羅埃西亞曾經聯合德軍去屠殺塞爾維亞人,到1990年換塞爾維亞人去屠殺克羅埃西亞,所以他們其實是半斤八兩。我們想在故事中找到一個平衡,我覺得要拍出一些超越人心的東西,不能很偏頗的站在其中一方。 - Q7觀眾:電影包含場景配置,可否就時間和歷史上的風格道具進行說明?
劉導演:當時在好萊塢很多人不敢接我們的東西,因為美國的美術很多人是大量接案子,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做這麼多的田調準備,於是我們想說找一位台灣的美術設計,語言溝通上沒有障礙,把設計圖和南斯拉夫的歷史花三天三夜向美術設計解釋,而美術設計本身也是海軍陸戰隊,所以對一些戰爭背景也有些了解。只要很簡單的補充一些歷史知識,配合克羅埃西亞歷史系教授背書的圖片和參考資料,帶著這些到好萊塢去找是否能借到,若借不到再找美術設計一一來設計及挑選,最後當然也會和教授確認我們設計出來的軍隊、槍聲配音、武器沒有問題再使用。
短波二:肉身與靈魂
主持:宜楹
來賓:貝莉小姐Ms. Belly (製片助理張儀同、張語軒)
朱文錦(導演林承翰、演員郭佩萱)
《出口:夢想肢戰》(導演潘瑋杰、主角哥哥吳景智)
- Q1主持人:請問朱文錦導演為何會想用真人演出金魚?
朱導演:朱文錦其實是去年宜蘭國際綠色影展的特別計畫,我們是學很久以前金馬做的「10+10」,因為我們經費有限只找到十位導演,又剛好宜蘭有十個鄉鎮,造就了另類的「10+10」。至於為何金魚要以真人演出,是因為剛好我們的演員郭佩萱當時染了一頭亮橘髮,一看也太像那之魚了吧!所以就這樣拍攝了。 - Q2主持人:請教《出口:夢想肢戰》的導演,片名中「出口」兩字對於自己本身或選手是否有甚麼特別意義?
潘導演:我本身也是球隊的成員,現在是球隊的隊長,這個問題可能要從我自己開始講起,為何我拍攝這樣一個故事。兩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拿不起最愛的玩具車,手都沒辦法動,各處求醫還是找不出原因,直到有一家醫院告訴我「你就回去等吧!會動就會動,不會動就不會動」,這樣的結果讓我非常無助。成長過程中遇到很多挫折,小時候吃飯別人都拿碗起來吃,但我覺得拿碗很不舒服所以低頭下去吃,因此被長輩罵像乞丐,或長大後被嘲笑「大小手」,那樣的聲音讓我沒辦法面對自己,甚至對父母親講為何要把我生成這樣,我不想和別人不一樣。直到2010年父親認識殘障棒球隊的教練,問我要不要加入,其實當時很不想做加入這個決定的,因為加入等於要告訴大家我是個身障朋友,而這個標籤在這個社會是很難被同樣眼光看待的。但大家如果看過《X戰警》或《大娛樂家》,有一群和你一樣的朋友或熱愛同樣的事物,我就很想看看他們發生了甚麼事情,所以我就站在球場外面看到有一隻手的朋友,他傳接球的速度像有兩隻手的一樣快,或是腳不方便的朋友一拐一拐地把每顆球接到撲到,那樣的畫面震撼了我,我也重新感受到自己是在甚麼水平上面活著。加入球隊後,我和朋友提到我加入身障棒球隊,但大家都沒有聽過「身障棒球隊」,在網路上搜尋也有只有找到兩家篇比較冷門的報導,所以我就開始作夢,在夢中自己是準備啟程的探險家,把探險用的羅盤指南針轉換成攝影機腳架。一直以來我都有很大的疑問「怎麼和缺陷共處?」、「這樣的我們到底在找尋甚麼樣的出口?」,於是我開始拍了這樣一個紀錄片。先在2012年完成了《出口》那支紀錄短片,於2016年再完成《出口:夢想肢戰》這部片,期望這樣的片子能讓我們重新去定義我們生命中的缺陷,也讓我們去找尋屬於自己的出口! - Q3觀眾:影片《貝莉小姐》內都是外國人、外國片,但影片製作是台灣人,想請問為何是以外國形象呈現?
製片助理張儀同:本片以國外雜誌為素材來拼貼製成,而貝莉小姐本身是不標準會出現在電影元素中的女性,身材短小、臉是肚子的型態。現在社會對於女性的標準很特別、很固定,要有纖細的腿、小蠻腰、豐胸。但為甚麼現在女性的標準一定要變成這樣?為甚麼其他人不能做出自己而要被市場淘汰型態?國外雜誌很常會把時尚標準做成雜誌,告訴大家現在最喜歡的審美觀是甚麼或最被世人接受的元素是甚麼樣子。那以雜誌拼貼的方式呈現,其實有種反諷、勸世的意味,其實美的標準並非由世俗制定,是由自己來評斷的。 - 吳景智(球員吳景傑的哥哥):吳景傑在去年初車禍離開,所以由我代表。跟著導演到處參加影展,其實希望景傑「每周從高雄搭車到台北練球,跌倒也要自己站起來」這樣從小不服輸的精神可以傳遞給大家!
短波三:日子還是要過
主持:馨婷
來賓:《漂流日記》(導演吳中義)
《無影無家》(導演楊凱諺)
《生活小悲劇》(導演蔡宜豫)
《奇遇》(導演王君弘)
- Q1主持人:各影片導演的創作發想或動機?
《漂流日記》導演吳中義:當時生活中發生了一些我很難去面對的事情,想趕快忘記那件事、變成回憶,或者希望他只是夢到的東西不曾存在我的回憶裡面。之後想說那乾脆做成作品,讓他留在這裡,大概是以這種感覺去製作。
A1-2《無影無家》導演楊凱諺:本片是我和另一位導演黃燕燕一起製作的。黃燕燕參加了芒草心社團,一個關懷遊民的機構,燕燕在一個跨年夜陪伴片中那位遊民賣大誌雜誌,才認識他,得知他當過放映師,也才開始有這個計畫。
A1-3《生活小悲劇》導演蔡宜豫:因為自己生活中常遇到諸如此類的悲劇,當我開始用照片記錄下來,再回頭看照片回想悲劇發生當下的焦慮感、回頭面對悲劇時卻覺得蠻有趣的,因此做了這個動畫。
A1-4《奇遇》導演王君弘:本片是我大學畢業的作品,拍這部片之前有先拍過短片,但當時因技術上的限制所以有些畫面並沒有拍出來,這次想在有限經費裡拍出長一點的片子,但又不知道能做到甚麼程度,所以過程中一直在一邊拍一邊寫劇本,慢慢找到自己的節奏來完成的。製作後期因資金不夠,導致作品長度有點尷尬,沒有很短也沒有很長,但我還是想維持這樣的長度,最適合當像想表達的作品。 - Q2觀眾:《奇遇》這部片給我的感覺是在年輕世代一直再找一個燈或找不到的狀態,但到片尾到賓館出現女生照片,好奇本片是否有愛情的成分?
《奇遇》導演王君弘:每個人都有一些關於照片的經驗,照片記錄了當下的東西,但情感隨時間改變,可能跟戀人有一張照片,但你們的關係結束了,再回來看照片的時候可能又有一種……我就是覺得說不太清楚,所以試著以影片的方式呈現。至於是否有愛情成分?對我而言,這已經是一個虛構的東西了,但我藉由影像和聲音的重組建構,或許會讓你(觀眾)有這樣的感覺,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 Q3主持人:請問漂流日記的導演是否受其他作品啟發而創作這個腳本?
《漂流日記》導演吳中義:平常有書寫的習慣,想以影片方式呈現,而那段時間剛好感受比較強烈,想說藉由把它做出來就把它忘掉,所以主要出自本身感受,沒有特別受其他作品啟發。 - Q4觀眾:無影無家的導演是否特別關懷遊民這個族群?為何特別想拍這樣的紀錄片?
在遊民身上好像有很多標籤,社會對遊民好像也有些成見,以前也有一些在龍山寺的遊民潑水的新聞,於是我思考「甚麼是遊民」,有一天想通其實就是「付不出房租」。我和燕燕導演想做的是,藉由訴說一個遊民的故事或許能是否能削弱這個標籤。而做到後面,這已經不只是一個遊民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電影的故事,藉由這位曾經當過放映師的街友他的故事,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電影的興衰,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的,甚至產生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 - Q5主持人:《生活小悲劇》中有許多特別的聲音設計,如擠壓或尖叫,請問導演對聲音創作上的想法。
生活小悲劇(導演蔡宜豫):其實做聲音是整個製作中最愉快的過程,有直接錄滴水的聲音或是嚐試以不一樣的聲音去對不一樣的畫面,如切到手時有電鋸的聲音,或人融化時配關門的聲音。曾經玩過一個小小實驗,先編輯一段聲音再做動畫,覺得蠻有趣的。
短波四:親密疏離
主持:馨婷
來賓:《自》(導演王俊為)
《超級壞貓 恋愛ゲーム單機版》(導演小貓肉球)
《有時飛、有時走、有時游》(導演李培㚤)
《一拉一》(海先生)
《註姊》(導演應蔚民)
- Q1主持人:各導演的創作動機及背景
《自》王俊為導演:碩一修了一堂電影製作的課,老師給了我們”觀察我”這個主題,對我而言,脫離不了我的家庭,所以就做了這樣的作品。
《超級壞貓 恋愛ゲーム單機版》導演小貓肉球:因為當時失戀了,想做一個作品來發洩這樣的情緒。觀察自己及身邊的朋友,發覺在戀愛的過程中心會變得很弱,心好像會被拿走,覺得這個樣子很像在破關打怪,因此做了這個作品。
《有時飛、有時走、有時游》導演李培㚤:在做為了劇情片去做場勘的過程中忍不住會去留意捕捉一些畫面,就想說那製成作品留下來吧!
《一拉一》海先生:我忘記了,但如果現在要說的話,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心存善念啦!
《註姊》導演應蔚民:自娛娛人! - Q2主持人:《自》這部影片給人一種異常疏離的感覺,是用王文興《家變》這個作品作為旁白,請問為甚麼會想做這樣的安排?
主要是來自於讀《家變》時的同感吧!因為他講出很多自己對家庭的感覺、父母跟孩子之間的關係。 - Q3主持人:請問超級壞貓的導演為何想到要用電動遊戲的方式進行創作?
小貓肉球導演:一開始決定要做這個題材就直覺想到要用電動遊戲,因為我覺得在失戀及復原的狀態就很像在電動裡面闖關,要打破情感的拉扯、過去的心結或心魔就很像打怪一樣,所以決定用這樣的方式去說這個故事。至於為何要用貓,是因為我的作品大多跟貓有關,那因為失戀了,心碎掉以後跑出一個超級壞貓,他其實是你的心魔,把你的心臟吃掉,必須在闖關的過程中殺那些戀人或戳破粉紅泡泡的事才能取回自己的心。 - Q4請問《有時飛有時走》的導演為何以台語當旁白?
導演李培㚤:這是一個動物消失的故事,不管是大自然的變化或是人為破壞,之前之後的差異我認為以長輩的角度來講會比較有說服力,而另一方面我想紀錄我媽媽的聲音,所以請她配音。 - Q5主持人:請問一拉一的導演為何想用此音樂家的音樂做使用?
海先生:其實音樂是用買的,而不是先去找到一個音樂家。當初音樂有四個版本,有些版本不滿意或買不到版權,在最後快放棄的時候終於找到這段音樂,所以說算是機緣吧! - Q6主持人:請問應蔚民導演為何用《情人復仇》這齣戲做為本片主軸?
應蔚民導演:小場live表演外的場域是很特別的,有點像印度電影院外的地方,觀眾會買票進來看電影,但他們想看電影就會進來、想出去就會出去,不一定會看完整場,但他們也了解劇情。而劇中角色、他們所做的事其實都是和《情人復仇》的劇情相關的。 - Q7觀眾:請問《自》的導演,片中的銅像是自己爺爺奶奶的銅像嗎?另外家人一起看的影片是以前拍的家庭錄影嗎?媽媽哭的點?影片中爭執是請家人錄的嗎?
王俊為導演:銅像是我爺爺在奶奶過世時做的,把自己也做進去了,爺爺還在世!錄影帶是爸爸以前拍的家庭錄影帶沒錯。媽媽可能感情比較豐沛吧,畢竟看到二十幾年以前的紀錄,可能有些人也不在了,有很多感觸吧!爭執的部分是我錄下哥哥與媽媽的對話。
- Q8觀眾:今天看到的影片都是比較喃喃自語,戲劇創作的部分只有《註姊》和送披薩的男生那段,有點失去了與觀眾的連結。甚至其中有一段是完全靜默的,一直看到貨櫃箱的畫面,我不太懂這樣安排的意義是甚麼,是在考驗觀眾的耐性嗎?還是這是一種新實驗性的電影形式?我個人認為如果要呈現一個作品的話,必須還是要有一些結構,但我不知道在座觀眾觀影的習慣是甚麼。我本身是學戲劇的,不好意思我說的比較直接,但我會看到前面一些作品的確還是非常不成熟。第一部《自》導演的場景配置其實蠻有趣的,比如說一開始有兩個銅像,後面不斷的有一些家庭出遊的照片,中間還有一些敘述或家人互相討價的一些事物,既矛盾又有衝突,帶出一點立體感,設計得蠻好的。只是說呈現的過程中不太有結構性,比較像一塊塊拼貼,所以我不太清楚你要表達的、主要的敘述是甚麼。我想說的是,如果未來想做一個公開放映的影展的話,可能還是需要顧慮到與觀眾的連結,會比喃喃自語來的更有趣一點。
- 海先生:我想請問這位觀眾,拍大巨蛋的那部有讓你產生任何感覺嗎?還是就跟貨櫃那段一樣?
觀眾:我覺得那部比較像紀錄片的手法,我會比較像一個旁觀者,比較沒有參與感。再加上沒有任何的聲音或現實聲音在運作,所以有點考驗觀眾的耐性跟……不知道,所以如果時間過長的話…這也是為甚麼有些戲劇電影,他們有些東西不能重複出現在同個片段,觀眾會疲乏、注意力會跑掉。如果這是一個實驗性的方式的話這是成立的,但如果是一個要跟觀眾對話的影展的話,可能就要考慮時間長度,不要讓觀眾的注意力跑掉。 - 李培㚤導演:其實游牧影展他的選片方式會跟其他影展不一樣,有分劇情片、紀錄片、實驗片,可能剛好我們這場主要是紀錄片和實驗片,比較沒有劇情的部分,畢竟我們也沒有去找到一些演員去做演出,加上我們的影片長度都在十分鐘以下,所以可能沒辦法讓你感受到戲劇的部分。但我們也會針對你剛剛提出的問題做思考,之後做紀錄片、實驗片的時候也會去思考如何去和觀眾互動。
- 海先生:當我們帶著一定的框架去看一個作品時,可能就看不到框架以外的事情。所以帶著劇情框架去看剛剛的那幾部片時可能就會覺得…what the fuck。我自己對《蛹》(大巨蛋)的那支,有一些共鳴,雖然他很慢,因為這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背景下的一個社會事件,大家都對他有關注到一個程度,在這個狀態下我們會被勾起一些想像。它其實沒有跟你講說「他覺得怎樣」,但根據你自己的生活背景,你會投射出一些想法。對我而言,片子前面帶到很多工人的畫面,會讓我想到雖然每天政府官員或民眾在吵,但其實都沒有回到真正在做這些事情、比較辛苦層面的人身上,這是我的想法。所以「放開框架」,活得比較快樂!
- 王俊為導演:我這個作品本身就是比較私人的東西,所以如果觀眾也如果能從中感受到甚麼的話,那…就差不多了,因為它也不是劇情片。
- 海先生:突然想到,在台灣這個創作環境下,其實要去得到足夠的經費去完成一個有劇情的短片是有難度的,但大家還是想要創作,所以可能會轉一個方式去闡述心中的影片,所以你看到所謂缺乏劇情結構的東西…不知道是不是和這個有關。
- 觀眾(2):其實這是一個關於私人和公共性的問題,一個對大巨蛋事件很了解的人,可能一個「大巨蛋」三個字的畫面他就能聯想五分鐘,這可能連結了比較私人的東西,但其他人可能就會覺得無聊。至於經費的部分,我認為成本最高的可能是手繪的那部吧!有小人在吹泡泡或小人在收割香蕉的畫面,雖然影片非常短,那是可以看得下去、很開心的影片。但這個東西就是牽扯到很多技術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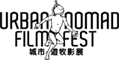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