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速記:《狂人波伊斯》全台首映,此座談邀請藝術史學者李雨潔和謝佩霓及藝術家彭弘智進行討論,從這場精采答辨與討論的座談會中,整理成五大點,幫助大家了解波伊斯。文字紀錄:高晨鐘;整理:遊牧影展。
- 關於《狂人波伊斯》
謝佩霓認為這部紀錄片做得非常嚴謹,尤其最近在台灣,很多紀錄片還是有太多的後製與加工,所以本來可以是非小說或非文學類的題材、主角(像波伊斯這項題材)往往會變成非常多過度的文學性描述與揣測,或用現在的眼光詮釋,卻沒有回到當時。
如果各位在大學教書或對波伊斯有興趣,這部片剛好可以當成歷年來最完整的「波伊斯傳」,藝術史學者謝佩霓認為這不是偶然,在美術史中,每三十年做一個總回顧的話,是可以看到更完整的印象。波伊斯在1986年過世,這部片子是在去年殺青、正式首映,所以也符合了在探討美術史,或者是說任何的歷史,用三十年來檢視的概念,某個層面也算是一種非常古典的做法。
- 波伊斯,你這「麻煩」的人物
波伊斯的作品非常多,例如他用毛氈做的衣服就有一百多個版本,然而他的作品都是有機的,經常發生長蟲或是腐爛的現象。英國泰特美術館(Tate Modern)曾收了一件他的衣服,因波伊斯已逝,收復師只好寫了一篇文章說明這件衣服何時長了蟲,用自己的方式修復這些腐蝕,所以波伊斯對美術館來說其實是個很麻煩人物。在德國甚至幾乎每個州立美術館都有他的作品。波伊斯同時兼具藝術家、政治家角色,但他的作品又非常感性,以他的毛氈作品為例,當你踏入德國美術館展間,遠遠就可聞到一種悶悶的、像自家地毯的味道,他的作品會對你的生命產生交互作用。
其實要拍波伊斯的紀錄片很不容易,波伊斯的遺孀Eva掌控代替丈夫表態的權利。她是一個八十幾歲的老太太,本身也是藝術史學者,當有人向她提出想研究波伊斯的藝術生涯時,若她評估對方對波伊斯了解不夠深便會回絕對方。《狂人波伊斯》導演Andres曾寫了一封信給Eva,Eva剛開始沒有回應他,後來他打電話給Eva,才知道她早收到他的信,但Andres要求的三百多件作品圖像授權中,有好幾個作品名稱都寫錯,所以她不願讓渡這個權利給Andres,溝通很久才爭取到拍片機會,所以拍這部片是個很辛苦的過程。
- 波伊斯與台灣藝術家:
謝佩霓認為波伊斯辭世對我們來講還有另一種意義。台灣在1987年解嚴,所以看完這部紀錄片,包括我們最近討論的種種時事,會讓你問一個問題:像波伊斯這樣藝術家在台灣可能存在嗎?若跟波伊斯用同樣的態度到時間,在他死後的三十年還可能造成一樣的回溫效應嗎?若當事人今天還在,他會如何面對自身這一切?
很多大家心儀的藝術家,特別是台灣或是亞洲這些當代藝術的大師,他們受波伊斯的影響其實很深,但奇特的是,大約十五年前大家不再談論他們受波伊斯影響,我們可以想想,台灣當時若尚未解嚴,第一批從國外帶著波伊斯這樣的思維,或引薦國外相關作品是有可能的嗎?現在大家熟悉的吳瑪俐、北藝大的校長陳愷璜老師、石晉華老師都受到波伊斯影響,石老師的菩提樹種樹計畫即是向波伊斯致敬的作品。如南部非常前衛的畫廊,或是像伊通、二號公寓,不只發起、營運,能夠堅持到現在其實都是受到波伊斯的啟發。
- 如何理解波伊斯的名言,「人人都是藝術家」?
波伊斯有一句名言:「人人都是藝術家」,這被紀錄片強調了波伊斯在政治、社會的角色,要如何去理解人人都是藝術家這句話呢?這句話其實是波伊斯在1974年一場演講上所言,後來也在自身文章寫到。大家好像都容易誤解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意義,就好像「你我都沒學過畫,但都可以是藝術家」。在激浪藝術運動中(Fluxus)就曾有藝術家寫書探討波伊斯如何作為社會改革者,他們曾提到:「每個社會上的人都不能逃避共同形塑社會的責任」,這個世界掌握在大家手裡,我們可以透過創意來改變社會,但改變社會並非藝術的目的,它只是可能影響社會的結果,所以這句話的意思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作藝術家。
針對「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概念,應該要被強調的是這句話後面的意義,也就是要在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之下才能稱人人都是藝術家。因為波伊斯不曾說過人人都可以是詩人、藝術家等等。在看這部電影時也應該要去對照介紹波伊斯的相關書籍,凡是適合影像的不必然適合文字,反之亦然。回到畢達哥拉斯所說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但台灣的教育都跟大家講下半句:「你覺得他是就是,你覺得他不是就不是」
- 波伊斯與作品
有德國史學家認為波伊斯的作品其實是為了創造「myth」,讓作品不會只是生硬的概念藝術,而是可以更容易地融入人類的宗教與文化,針對波伊斯《如何向死兔子解釋繪畫》這部作品中充滿許多薩滿元素,原來是當這部作品在畫廊演出時,牆上都掛著波伊斯的畫,波伊斯臉上塗著金箔跟蜂蜜,金箔為智慧的象徵,蜂蜜代表豐饒、新生,他當時帶著一隻死兔子看這場展覽,並拿這隻兔子的爪子去碰每張畫,波伊斯說:「跟兔子解釋藝術觀念可能比跟人類來得容易」,而這裡頭也可以看到許多「myth making」。
也有學者提出,「如何看待波伊斯作為社會改革者的角色」,認為在波伊斯的作品,如七千棵橡樹探討的並非環保,亦或大家透過社會參與來改造城市,其實主要目的是把平時沒有交集的人聚集在一起,達到藝術溝通與流通,因此社會雕塑本身並非全然為社會改造。很多人認為六、七〇年代透過波伊斯社會雕塑的概念開始了「藝術即政治」這件事情,其實這可能也是另一個迷思,因為根據朗格的研究,波伊斯並沒有開展一個新的美學角度,其實這從二十世紀初的avant-garde就已經有了。波伊斯只是延續了一些現代主義行為藝術的思維。最後我想再補充一下社會雕塑的概念,在七〇年代時,波伊斯就在一些文章中提出他要透過社會雕塑來改革社會,社會雕塑可能時臨時的組織、大學之外,它其實是一種社會參與的隱喻。因此波伊斯七千棵橡樹的作品其實是想表達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個人來改變社會。
其實波伊斯已經說過他做的藝術行為若已經完成,再去追究是一種「浪費」,至多也只是一種紀錄而已。波伊斯這樣的理念也很類似東方禪宗思想,好似「我已經過河了,又何必要一直背著我不放呢」而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六、七〇年代對東方「放下」的思想重啟的可能性與受其的影響。謝佩霓最後總結她的看法,她認為欣賞任何一部電影、文學作品、藝術品就像是在漫遊,要相信自己走得出來,不然你根本走不進黑森林。而她認為波伊斯所追求的還是一個有機的藝術發展,這些作為看似還是以人為參與,但最後還是必須回歸生態的一部分,而每個人都會造成這個生態的質變,所以用他的一句話總結:「藝術應該要是有機的」,就像波伊斯到最後還是相信民主是一切及「以人為本」的概念,波伊斯本人也說他最大的作品就是「當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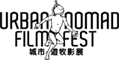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