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請導演們自我介紹,並說明一下各自影片的靈感
陳(陳凱法):大家好,我是第一部片《製琴師的南方飛行》的導演陳凱法。我在台東看表演認識漂流出口,本來只是幫他們拍個照,後來就愈陷愈深變成他們樂團經哩,至今已經快三年了。和他們一起從拍照、表演、練習到籌備專輯,一路上發生很多奇怪有趣的事情,可是太多事情我無法拍啊!因為我也是其中一員,我也不可能再用什麼方法重現,所以就趁這個機會,剛好Kanji老師本來就很會講很多大道理,我就用旅行日誌的方式一邊問他,一邊紀錄,再搭配一些之前練團的畫面做成這部片。我是在過去採訪工作中認識Kanji老師,覺得他很厲害,就邀請他來看漂流出口的演出,他聽完不發一語,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帶他去台南玩,回程的路上,團員們在車上唱起了原住民古調,那種純粹的聲音感動到他,讓他開始改觀。就像他在影片中講了很多關於聲音的中心,其實說到底不過是讓音樂回歸到人心。
李(李永超):大家好,我是《挖洞子》的導演李永超。我其實也沒有寫好完整的劇本,我是一邊拍一邊寫劇本的。當時是我回鄉過年,剛好聽我弟弟這幾年在做挖玉石的工作,那個地方我過去也沒去過,剛好那陣子狀況還OK所以我就和他一起進去逛逛,去到那裡我才真的了解他們真實的工作狀況。拍攝上遇到最困難的地方是因為那裡所有人都在工作,所以有時要請他們停下手邊工作讓我拍攝,同時又要小心不要被監工逮到,這方面真的比較緊張。這部片是以手機拍攝而成的,主要是因為如果我帶攝影機去到那裡,可能路上就會遇到很多刁難,而且本來也沒有預計要拍,就是以一個觀光客的樣子去逛。我的下一部片也會是關於我的弟弟,給他挖玉石故事一個總結。
王(王念凱)大家好,我是《白日夢》的導演王念凱。我本身是作後期的特效師,拍這部片本來主要是想和朋友一起拍片玩一些東西。一開始的發想是關於「城市的異想」,但是我比較不想著重在城市的部分,所以我找了一個人物進來,我開始思考什麼樣的人會是以想像在過活的。直到有一天我半夜下班,在路上看見一個盲人,他走在大馬路正中央。我就在想,他會不會其實並不認為自己走在大馬路中央,而是走在一個自己設想中比較安全的路上,於是我開始揣摩盲人所想像的世界是什麼模樣。我只是想做一個輕鬆好玩的東西,而沒有特別想要將重點放在背後的議題上,所以之後也不會繼續在這題材上做揣摩,那樣會變得有點在消費這個族群。
應(應政儒):大家好,我是《犧牲之旅》的導演應政儒。我的靈感李又鸚鵡鵪鶉老師就坐在後面,我的上一部片《晃遊身體》之前也在遊牧放過,那部片是以李大師為主,但啟發的事件並不是他,而這次這部則是相反,他只是客串,但靈感的啟發卻是來自之前在拍《晃遊身體》時,和李大師很多的深入訪談。透過這些訪談而有了一些想法,在沉澱了一兩年之後,才有了這部片的構想。《晃遊身體》是一個比較實驗性質的前衛影片,並帶有一點紀錄片色彩。這次想說自己過去都是以實驗片為主,很少做過劇情片,想來給自己一點不同的挑戰和嘗試。但我也不希望做一個完全很敘事的東西,因為這個故事本身是很八股的,東方就是梁山伯與祝音台,西方就是羅密歐與茱麗葉。所以我會希望有多一點敘事風格的挹注。
Q 想請問應政儒導演,您的畫面處理的非常美麗,每一場都像是一幅精緻的畫。請問您創作的過程會畫分鏡先設計好畫面,還是到了現場看了場景臨時發想?還有想請問片中的湖拍攝地點在哪裡?
應: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學美術出身,從小就學畫,所以我對畫面會有很多執著,會希望所有鏡頭都可以達到我的要求。但《晃遊身體》比較沒有,它比較自由,畢竟它某部分也是紀錄片,所以會有很多即興發揮,畫面處理也都是比較即興捕捉。我自己是會畫分鏡,也幾乎會按分鏡來拍,但我一直合作的攝影師,他會幫我補一些空鏡。婚紗的湖是在夢湖拍的,那裡同時也是《共犯》的拍攝地。影像上我也有受很多前輩導演影響,例如:安哲羅普洛斯、塔可夫斯基,還有我前期很討厭的王家衛,《一代宗師》的畫面和美術真的影響我很深。
Q 請問《挖洞子》的導演影像顏色後製有做什麼特別的處理嗎?
李:原本手機拍攝出的色調比較淡,我有特別調得鮮艷一點。
Q 請問《犧牲之旅》當中的澡堂是在哪裡拍攝?澡堂有什麼特別的象徵意義嗎?
應:是在台北機廠拍攝的,那裡非常難借,我是在開拍的第二天才借到的,所以除了落葉和水之外沒有多做任何加工。我覺得李大師就是一個既熱鬧又有強烈孤絕感的人,那時候一直有一個畫面,是他在一個很黑的澡堂,他在那樣的場域間洗頭,週遭播著一首歌,原本想的歌是情人的眼淚,他帶著一個破舊的隨身聽,和另一位年輕男子在同個場景,但是沒有任何交集。透過倒影和光影的交錯,就像他們終身無法實現完整的感情。我就是從這樣的畫面去發想了這段故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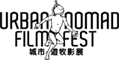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