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耿瑜、Eden
與談人:辛建宗 《澤水困》導演、劉家欣 《凡凡》導演、陳欣緯 《辦桌》導演
題目:故事發想 – 劇情背後的真實
Eden : 首先想要了解劇情片有什麼吸引你們的地方?
劉家欣導演:關於影像的創作方向,沒有設定一定要是劇情片,一開始我也有拍比較實驗性的錄像、影像詩的作品,也接觸過紀錄片,到後來才想試試看劇情片。劇情片有一個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可以說出紀錄片沒辦法傳遞的東西,它可以先被寫成劇本,被排演過再發生,後來就開始了劇情片這樣的創作方式。
陳欣緯導演:我大學時是念電視製作,到研究所才開始拍電影,在我研究所漫長的六年之中也都在做實驗錄像比較多,《辦桌》是我少數創作的劇情片作品。除了做過電視、電影,其實我現在的工作是在做動畫,所以對我來說不同的媒材有各自獨特的表達方法,都只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辛建宗導演:當初我到台北電影節也是帶著實驗片,但跟大家不同的是我一開始是拍廣告,累積的經驗是非常商業性質的。拍久了後發現影片這個媒材還可以做很多的描述,有很多的表達空間,所以就有點「轉性」了,開始拍一些非常奇怪的實驗片。而現在做劇情片,對我來說像是提供了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是虛構卻又真實的。我們在製作的過程中也進入了這個世界,是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其中會遇到很多困難不可能,但世界成真了,更有趣的是當你把這個世界放在螢幕上,會吸引到外界的人而產生了交集,我覺得整件事情還滿有啟發性的,這就是我喜歡做劇情片的原因。
王耿瑜:我這兩天在看一本Robert Altman的書,書名叫《不要給我講故事,我需要的是人物:認識好萊塢導演羅伯特.奧特曼》。關於人物這件事情,根據我跟片的經驗,大學時跟過侯孝賢導演《尼羅河的女兒》,一個跟台北年輕人有關係的故事,侯導是非常寫實的導演,但對他來說年輕已經有一點久遠,所以當時導演組每天的工作就是根據初稿劇本裡的角色,牛郎、混夜店的大學生、各式各樣的角色,安排這樣的SAMPLE去跟侯導聊天。後來我發現不只有寫實片的導演會這樣做,像王家衛導演在拍武俠片的時候,也花了一、兩年的時間做這樣的功課,所以很好奇幾位怎麼開始發想及琢磨角色?
Eden : 回到這次的主題,很多時候虛構的事情都來自於真實世界,幾位導演在發想故事的時候一定有受到生活上一些靈感的刺激,想請導演們分享一下這次劇本故事跟真實生活之間有無關聯?
劉家欣導演:剛好身邊有一些朋友在酒店工作,我對那個地方也很好奇,當時正在做研究所的畢製,必須非常認真做田野調查,所以除了看很多書和訪問酒店公關的資料,也因為朋友的關係認識很多經紀人(類似媽媽桑的角色),訪問到好幾位姐妹,也剛好有機會能到裡面去,花一個晚上實際進入酒店實習。我那天是做服務員的工作,可以帶位和進去看大家都在做些什麼,所以我的故事混合了很多朋友的故事和當天看到的細節,因為我覺得細節是劇情片很重要的部分,寫本時可以清楚的想像角色或劇情的走向,但對我來說細節的描寫比較難掌握,比如說他們的樣子、氣味、應對的方式,如果我從來沒有待過酒店,我認為我會沒辦法掌握真實性,所以一開始必須在田野調查的時好好記錄和觀察,才能捕捉到這些最真實的東西。

王耿瑜:那是先有了劇本大綱才去田調?還是先去田調才發展出故事?
劉家欣導演:我是先寫了故事大綱和劇本,從朋友的故事改編,等要拍時才發現有很多地方太過模稜兩可,太多想像不太真實,包括選角時要找怎麼樣的人、他的「氣」是什麼,我一開始很難掌握。如果我沒有去過的話可能會拍出一個很飄渺的影片,所以田調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陳欣緯導演:以《辦桌》為例,是從我奶奶的故事改編,因為我奶奶本身是在客家莊裡辦桌,但不一樣的是我沒有只講她這個人,我還採用了我媽媽天主教的背景。我從小生活在身旁都是客家人的環境裡,同時因為媽媽的宗教關係,我從小就受洗為天主教徒,偶爾會上教堂做禮拜,但也會跟著奶奶拿香拜土地公、普渡等等,但就我所知有些天主教徒是不被允許做這樣的事情的,到大了我才認知道我背景的不同,開始覺得有趣才去探究這些事情。
在準備拍《辦桌》時,一開始醞釀劇情希望把穹林—我生長的地方,在我記憶中的樣貌真實呈現出來,希望把奶奶辦桌的職業當作主軸,也希望把宗教的東西放進去。至於田野調查的話,因為我的主角等於是我的長輩,平常老人家聊天話題也多圍繞在平常吃哪些藥?身體哪邊又痛?兒子女兒有沒有回家啊?就是對他們多做觀察這樣,也是有了田調才讓我的劇本能更接近真實和生活化一點。
辛建宗導演:一開始耿瑜提到那本關於角色的書,讓我回想起我當初為什麼要做電影。相信在座各位生命中可能有一部電影讓你覺得怎麼那麼好看,因而起了想要拍片的念頭。我小時候是生長在公務員家庭,從沒想過要拍電影,一直到了大學之後,和女孩去約會去看了《新天堂樂園》,就是這部電影讓我覺得原來拍電影能這麼有趣,也讓我和電影開始產生一種連結。關於新天堂樂園吸引我的地方,第一就是角色之間相等的強度,這也是我之後做故事片最在意的核心,第二就是形式。我經常在進行這樣的抉擇,關於電影要以形式為主還是要以角色為主,畢竟兩者表現的重點不太一樣,但隨著故事發展最後我還是會回到角色本身可信度的問題,所以我其實滿贊同剛剛耿瑜提到的這個部分,關於角色的重要性。
王耿瑜:辛導演的片子是從易經的卦延伸來的,覺得很厲害可以用這樣的故事和結構去表現,所以是先有了關於「易經」這樣的形式再去發想內容?還是反過來?
辛建宗導演:對我來說創作之所以有趣,就是它必須要有趣才有繼續下去的可能。我想分享關於我在剪輯影片時的例子,有時候我在剪一部片,我心裡可能會先有一個高低起伏的節奏,剪完後才去找配樂,也許我的段子四分鐘,我就會剛剛好找到一個跟我每一個節奏都和拍的四分鐘的音樂,就是這麼神奇,影像和音樂是可以同步的。我覺得創作有一部分的有趣是在於這種有機的組合裡,像我這部《澤水困》,是非常奇怪形式的片,故事的發生也很奇怪,只是剛好我們這群工作人員那時候都沒片拍,前陣子也接太多商業片拍到有點噁心的地步,想說是天意叫我們來創作的,想要完全沒有目的的創作,才拍了一個關於水、被水所困的故事。做完之後才回頭去想片子到底是什麼,才發現了易經的這個卦,跟我找到音樂是一模一樣的感覺,這個卦跟我的片的元素完全符合。

Eden : 導演剛剛有提到發現了謀和的卦是一件很雀躍的事情,但創作過程中一定有一些比較困難的地方,比方說沒有靈感、或是一些現實層面的問題,當遇到這些狀況的話會怎麼解決?
陳欣緯導演:現實的問題就是錢吧~因為沒有錢就真的沒辦法執行,相對於辛建宗導演當初拍是沒有目的,但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要畢業這樣,所以拍片是必須完成的事情。我的做法就是先去工作存錢、和家人借錢,寫劇本時也不自覺想說這個場面太大會不會超過預算、碰到死亡的場景有沒有需要辦喪禮等,諸如此類現實的考量,我想這是像我們獨立製片製作時會遇到的困境。
Eden : 那在劇情發想上有沒有遇過靈感卡住的狀況?如果有的話是怎麼解決?
陳欣緯導演:一開始劇本就是從祖母發展再加入天主教的元素,發展劇情前我先想結構要怎麼把這兩者串連,後來才著磨出用「食物」和「儀式」兩件事之間的關係去串起整個故事。辦桌就是儀式之後的一桌食物而已,進而延伸出超脫原本為了溫飽生存之外的意義,就像天主教的彌撒一樣,一塊麵包經過儀式後變成聖體。是先有了這樣的架構之後才漸漸把肉填進劇本裡。最常卡住的地方是在於劇本要如何忠實的呈現真實,不希望有太多強烈的情緒起伏這樣。
劉家欣導演:我卡住比較多地方是在於劇情片很容易變得很假,要如何找到真實,我總期待會有這麼一個靈光乍現、很靈性的時刻,但寫完劇本看了同樣的故事已經十幾遍都沒有感覺了,所以解決方式是我會開放很多彈性空間給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希望在前置的時期能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可以彌補我的不足和製造新的火花。
像我的故事裡有講到愛情,關於愛情從開始到幻滅的過程要如何用比較抽象的方式去講,我一直想不到,很焦慮因為快要拍了,我就常去散步,因為發現很多生活經驗都是從散步中得來的,有一次無意中看到一個路人在玩一個遊戲,把一個東西射到天上,我當下覺得這太美了,不管是誰在玩都可以流露一種非常天真自然的神情,後來我就把它加到我後天要拍的場景裡,如果沒有這些生活經驗也不會在故事裡有這樣靈光乍現的橋段,所以在創作的時候我喜歡打開很多開關才能接收到一些特殊的東西。
王耿瑜:這些年我越來越發現當下看的電影或遇到的人都可能反映出你自己,俗話說「相由心生」,想問導演們覺得作品跟你們當下自己的狀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陳欣緯導演:這個問題我比較難回答,因為我沒有立刻開拍,一方面是資金問題再來是我覺得我還沒準備好。所以一開始我是先架好劇本結構後,就放旁邊先去上班了,剛剛提到靈光乍現的時刻反而是在我抽離它的時候出現,經過一兩年後可以有更客觀或不一樣的想法。
王耿瑜:這個想法是從你奶奶去世後才有的嗎?
陳欣緯導演:其實不是因為我奶奶去世,是因為我從小就看著我奶奶和隔壁的叔婆辦桌好幾十年了,國小或國中的時候叔婆去世了,那時候的我也不太理解去世的意義,感覺就像一個人突然不見,辦完喪禮後看到奶奶一個人坐在客廳裡瞪著電視,我知道她沒有在看,這個畫面一直到我要寫畢業劇本時就冒出來,讓我開始想奶奶是在什麼樣的狀態裡思考著什麼,也許她在等待自己的死亡。
辛建宗導演:生命其實就是這麼長,不可能每一個靈感都有機會寫成電影,到後來只能去整理哪一些感覺是值得花費生命去做的,因為每一個靈感其實都頗強烈、頗平均,但隨著年紀漸長,會知道你沒有這麼多時間去做這麼多事,對我自己來講會接受這樣的事實,相信做這件事情都是當下最好的選擇,當你花了力氣拍出一隻片,他就是一個世界,也許當我們都死了千百年,這個世界是會留存千百年,我會這樣去催眠自己這是一件超級崇高的事情!這樣才有力氣去應付拍片會遇到的各種困難。
劉家欣導演:我其實都選我自己有感受的角色,像是有通病、或是想要認識這個人的心情去做創作。因為我是台北人,某種程度來說台北人有種疏離感,習慣不去表達情感,現在會逐漸覺得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誠實面對自己,以及不戴面具去面對他人,像剛剛提到儀式這件事情,其實像愛情或其他東西都是種儀式,都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證明其實自己還是有能力感受的,感覺其實一直都在,只是我們沒辦法好好的去正視它,這其實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Eden : 就三位導演的經驗,能不能給台下的聽眾一些關於創作的建議。
辛建宗導演:就像我剛剛所說的,我已經被污染過了。但以我十幾年前的狀態,就跟現在的你們一樣,如果有了想法,能不能成為電影都是緣分,不要對自己太苛責,他有可能不會成真,甚至只是個回憶,但有些事情無論結果都值得一試,像我做廣告認識很多導演幾乎都想要拍電影,可是一百個人裡可能只有一個會真正去拍,他們並不是不會,講難聽一點就是不夠愛電影,所以不會付諸行動。所以對於任何一個行動的人我認為都值得尊敬,無論成敗,光這件事情就已經很美好了。
陳欣緯導演:我想是因為個性的關係,看到什麼事情都覺得很好玩。大學畢業後去拍了一陣子的巧虎琪琪,還做過宅急便,因為一直覺得快遞這件事很浪漫,當下會覺得這些事沒什麼,就只是一份工作,但之後回頭看都成為我的養份。像當快遞的時候會覺得每開一扇門就是一個故事,這件事情真的非常浪漫,所以我覺得多接觸多觀察,搞不好這些故事之後都能成為一個完整獨立的故事也不一定。
劉家欣導演:我覺得這次最有趣的地方是因為獨立製片,所以我想把我的朋友都放在影片裡,我還為此辦了一場派對,找了DJ,讓大家在裡面跳舞,也當成片中一幕場景。這次讓我學到開心的工作,雖說是拍有點悲傷的故事,但過程都是很開心的,我之前的創作會比較戰戰兢兢,擔心很多事情。如果說每一次都是要實驗一種東西,那這次就是要實驗開心。希望大家也能用開心的方式來做作品。
Eden : 那王老師有沒有想建議大家的地方呢?
王耿瑜:像剛剛辛導演講的,其實藝術說到底就是一種催眠,創作者得先催眠自己在才能去催眠別人,我認為創作者一定要讓自己有所感,才能讓大家感受到。希望大家這幾天把握機會看片,感受一下三位導演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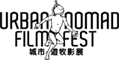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