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遊牧影展開幕片選映中國人權議題紀錄片《流氓燕》(Hooligan Sparrow),由於本片遭到中國官方封殺,巡迴超過30個國際影展之後,本次是首次在華語世界中與觀眾見面。除了導演王男栿本人出席映後QA,新疆籍中國民運人士 —吾爾開希、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 —楊憲宏先生也特別到場,與觀眾一起目睹這場令人不忍直視的人權抗爭現場。
吾爾開希:「我相信多一雙眼睛的圍觀,終究會形成某種力量。」
「一部好的紀錄片,很難不讓人投入情緒,這一部則是很難讓人不生氣。我是個維吾爾人,David (影展策展人)跟我一樣也遊牧到了台灣,不是為了躲避迫害,而是為了追求自由,就像現在屋子底的所有人一樣。
「這些年在我自己的遊牧生涯裡,對自由這件事有深刻的體會。不要害怕,是最能給人強大力量的一件事。但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世界上將近六、七十億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而這部紀錄片成功地呈現恐懼之下的人民、以及製造恐懼的那些人。」
「我很喜歡紀錄片裡的一個人買了部照相機,說「當你無力的時候,紀錄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像王導演今天做的事一樣。透過影片我們共同目賭這場暴行,就像在旁邊圍觀一樣,哪怕在距離幾千公里之外的真善美戲院裡,我相信多一雙眼睛的圍觀,終究會形成某種力量。讓暴行攤在陽光下,總有一天善良的力量能夠取代這樣的暴行。」

楊憲宏:「我想台灣必須成為人權的諾亞方舟。」
「我今天很震撼的是王導演非常勇敢的拍攝下來,我過去訪問過每一個被公安對付過的情節都是這樣。其中有一位高智晟律師,他手寫的書被我們偷運出來,下個月即將在台灣出版,那也是一個血淋淋的故事。」
「我剛剛遇到王導演,跟他提到希望在台灣儘速通過難民法,很多人我們也許救不到,但台灣必須成為人權的諾亞方舟。另外同樣重要的事,就是像王導演所做,識別每一個人權受害者,以及列出人權侵害者的清單,這是我們計劃內的事情,要在未來一年內讓大家看得見。」
觀眾提問
Q1 很好奇導演在最後是如何把素材運出中國的?
當時我嘗試了很多方法。首先想透過中國快遞,但因為被跟蹤的關係,很擔心前一分鐘把包裹寄出去,後一分鐘就會被沒收。最後是讓我當時剛好要去美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分批帶出去的。
Q2 想了解是否有被鏡頭遺漏但同樣精彩的故事?
電影只是其中非常小一部分,真實發生的事情仍然可怕的多。我曾經眼睜睜看到警察喪失人性的毆打維權人士,因為錄影的話我也會被打所以我沒辦法錄下來,很多時候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這些事發生,這讓我很憤怒。
另外有一些小插曲,比如說我和王宇有一次試圖去探望葉海燕,當時有兩位便衣警察騎著摩托車跟蹤我們。王宇建議用走他們跟蹤起來會比較困難,所以我們就沿途走走停停。最後那兩位便衣也不耐煩了,直接走到我們面前說「兩位美女到底要去哪裡?我們的工作也是不好做,是要拿工資向上級呈報的!麻煩體諒一下我們,不如直接告訴我要去哪裡,我們載你一程吧!」(全場笑) 也讓我理解到關於做這些工作的人,有時候內心並不邪惡,只是在那個環境當下才做了這些事。

Q3 導演對未來有什麼打算?現在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近幾年我打算留在紐約。對我而言最壞的結果有兩種,一種是流亡在國外回不去,另一種是回去了但沒辦法離開,這發生在很多維權人士身上,不是被抓起來、就是護照被沒收禁止出境。因為我的家人還在中國,這兩種情況對我而言都很糟糕。
Q4 似乎有在報導上看到王宇律師參加《流氓燕》美國首映的消息,不曉得王宇律師有沒有看過你剪完的最後版本,還有他現在情況怎麼樣?
王宇並沒有去美國參加任何放映的場合,但他有看過初剪的版本。那時候他在北京還有自由,看完後覺得非常感慨,說很高興你們把整個過程記錄下來,但傷心的是這只是千萬個案子其中的一個而已。
他現在的情況是沒有任何人能會見他。他原本有兩位律師代理,但政府發了公文聲明王宇本人不希望由任何律師代理,並附上王宇的簽字。但大家都認為那不是他的簽字,又或是在酷刑逼迫下簽的。在國外有很多人都在呼籲釋放王宇以及其他被捕的律師,七月九號快要到了,是他被捕的一週年,目前還沒有很大的成效。
Q5 導演如何處理恐懼的問題?當時是否有資源或他人能夠諮詢?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也沒有維權人士朋友。每一天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衝擊,我非常害怕,可能跟我缺乏經驗有關係。葉海燕和王宇都身經百戰,表現很鎮定。有時候我會放台相機錄我自己,說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這相當於我消除恐懼的辦法。
另外就是跟王宇、葉海燕聊天,我非常敬佩他們,儘管天天生活在這種恐懼中,也繼續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這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激勵。他們是要繼續在這裡生活的人都不害怕,而我是有出路的人所以就更不應該害怕了。更大的恐懼是想到如果我不拍下來,恐怕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那股動力是在我最害怕的時候,支持我繼續拍下去的原因。(全場鼓掌)

Q6 影片當中出現許多人從旁提供的資訊,如何辨認訊息的真假?
信息我覺得是靠直覺。每個人第一次跟別人接觸時都會有一個這個人可不可靠的判斷。當時律師也建議我不要用真名,但我完全不習慣所以我還是用了真名。有所保留的地方是我不會輕易告訴別人我的真實身份,對不熟悉的人我會說我是來體驗暑期生活的大學生。
Q7 影片當中出現很多的便衣警察或秘密警察,他們的身份是有經過查證的嗎?還是只是來自導演主觀的判斷?
關於便衣警察當然沒有證據,在當下我也沒辦法即時確認他到底是路人還是警察,反而是回去剪輯素材時才會發現,比如看到有人一直在對我拍照、或同樣的人在不同工作天裡重複出現。
Q8 一開始拍的動機? 之前有心理準備會面對怎麼樣的事情嗎?
我一開始想拍性工作者。我在農村長大,看到很多農村婦女沒有受教育的權利,找不到工作後從事性工作而備受歧視。當時找葉海燕也是因為他做了很多性工作者方面的維權,希望可以透過他認識一些小姐。但當我回到中國,葉海燕告訴我他很忙於海南的抗議,於是出自好奇和想要了解真相的決心,就決定跟著他一起去海南,到了那裡所有事情才開始變化。拍之前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也不知道事態會如此嚴重。
Q9 導演之後有沒有繼續追蹤女權或性工作者方面相關的計畫?
這兩年還不會回中國,而且現在正在美國拍其他片子,所以暫時還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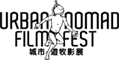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