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影展與Club-Mate聯名合作B-Panel:關於音樂紀錄片的一場座談會,繼與主持人張鐵志、《B級片:地下柏林》電影主角Mark Reeder、導演Klaus Maeck與策展人David暢聊八零年代西柏林後,下半場,我們加入《Wacken傳奇》單元導演、《藝術戰爭》導演Marco Wilms,及《蚵仔寮漁村紀事》、《離岸堤》導演施合峰,從音樂電影的角度,帶大家進入電影製作實務。
Marco Wilms: 《Wacken傳奇》在拍攝時,想以3D效果呈現,因為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重金屬搖滾音樂季,每年大約有10萬人去玩。一開始想用3D呈現是希望可以帶大家去感受、聞到那個味道,或接近親身體驗的感覺,同時也是帶點實驗精神的角度去拍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音樂。音樂其實也是情緒的催化劑,像有些電影會用不同的技術去表現,可是這部電影本身就是以音樂為主軸,希望可以用音樂去呈現、感受,捕捉當下的氛圍。
我本身雖然是紀錄片導演,但常以音樂為先決條件去剪輯。搭配一個畫面時,會先想到的也是音樂。等到音樂配上後,才會想到加對話等。我的另外一部電影《藝術戰爭》也有非常多的音樂元素在裡面。
Klaus Maeck:我非常認同音樂是很重要的元素,紀錄片或劇情片都一樣。很多人常忽略音樂,剪輯完才會想說:「啊!忘了加音樂。」因為我本身也是個音樂發行者,有時會有團隊來跟我說:「我們沒有經費了,能不能請你免費給我們音樂版權之類的。」我覺得最好的辦法不是這樣事後才這麼做;而是事前就要想到要如何為場景編曲、情緒與音樂怎麼搭配。
張鐵志:當時為什麼會想要拍《蚵仔寮漁村紀事》?
施合峰:我本身就滿喜歡音樂的。大家應該都知道,蚵仔寮漁村小搖滾是一個漁村裡的音樂季,那反差一開始就吸引我,所以我會想拍攝。不過,我跟他們做的影片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可能在於,音樂祭在我的影片中不是個重點,我不是為了音樂祭去拍這部影片。我比較想知道的是:他們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辦這個音樂祭,而且他們全都是門外漢,辦音樂祭會遇到什麼困難跟擦撞什麼火花。
張鐵志:所以你是拍一群人在辦這個音樂祭?
施合峰:嗯。我比較想知道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張鐵志:你也是音樂迷,如何選擇音樂?
施合峰:你還是會依照影片的調性去決定最後會使用的音樂。很顯然地,由一群外行人辦音樂祭是件很熱血的事。剛好樂團拍謝少年和蚵仔寮的關係很密切,他們跟我說,如果有需要的話,他們可以提供音樂給我使用。我覺得很適合,所以用了他們的音樂。
(觀眾問答)
Q:《塗鴉與革命》是部紀錄片,像導演拍了這種還會持續發展的議題,下一步是什麼?
Marco Wilms:一開始很多人問我說:紀錄片就這樣結束了嗎?不再拍續集嗎?對我來說,我就是把我想要說的話,想要呈現的東西表達出來後,這就是ENDING。《塗鴉與革命》這部片描寫阿拉伯的政權政壓,但就因政權的強迫下,很多創作者被迫要逃離國家,或是被迫轉到別的產業。其中有個藝術家逃到挪威,也有些藝術家本來在做音樂,他們可能就不能再做音樂。
張鐵志:其實這問題也可以問合峰。這問題就像在問,歷史正在進行中,你要怎麼去表達?蚵仔寮漁村小搖滾的後續為何?
施合峰:《蚵仔寮漁村紀事》有幾個主要人物,他們跟當地的關係成為影片重點。他們舉辦了這個音樂祭,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當我要拍下一部片的時候,我會面臨一個問題:「你要再重拍一次一樣的紀錄片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我們不會再重做一樣的題目。因此你必須要找到另一個切入角度。
在《離岸堤》中,我們把重點轉移到蚵仔寮的國中學生。也就是說,在他們去年辦的音樂祭裡,有個表演是由蚵仔寮國中的孩子去演出舞台劇,主要是希望透過這些同學的舞台劇表演,加強對於自己故鄉的認同感及自信,所以這個行動在整個音樂祭裡變成一個重點,那也是這個音樂祭不同於其他音樂祭的原因,因為他們著重的不只在搖滾音樂這塊,而是他們跟在地的連結。
Q:這個時代有很多音樂紀錄片正在拍攝,除了電影圈,也有樂團想要發行音樂紀錄片,因為在這個數位化的時代,CD不是很好賣,如果你拍攝一部紀錄片後,反而會有一些商機,或巡迴演出的機會。想問導演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你們要怎麼去拿捏?
Marco Wilms: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我就是以音樂家、藝術者為主軸,會以他們的心路歷程去看,不會想到其它部分。像其中一個過氣的搖滾樂團,他們非常有名,但後來卻被遺忘,因為我們的拍攝,可以讓他們再回到舞台,我覺得這是很美、很有意義的事情。但是那些為推廣而推廣的商業音樂紀錄片我並不是很喜歡,我會覺得那些製作人是以不對的角度去看待片子。

Klaus Maeck:對我而言,情緒和故事在拍攝紀錄片時是最重要的。像是我在拍攝《B級片:地下柏林》,並沒有想太多。雖然它是一部音樂紀錄片,但同時也是在講述西柏林當時的故事,所以我以「故事」為主軸去拍攝。我覺得帶著一些對比或是一些衝突去拍攝是不錯的,像藝術家在創作時,常帶有一些悲劇性的思維,他們就是因為不滿,所以感受到一些沮喪的情緒,才會把這些情緒轉換成藝術。紀錄片另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真與假的差異性,還有難辨性,這會讓觀眾覺得,「這是真的存在嗎?」會激起觀眾的情緒還有疑惑。就是這樣的疑惑讓人覺得很不一樣。
張鐵志:《蚵仔寮漁村紀事》提供沒去過蚵仔寮的人,一種認識它的方式,導演捕捉了他想要呈現的東西或是改變我們對那地方的認識。想了解電影對音樂祭本身有什麼樣的影響?
施合峰:我自己不是很清楚,因為我只是想要把它拍下來,每支紀錄片都是導演的觀點,所以不會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客觀的。只是說,我盡可能把我的感受透過影片去傳達給觀眾,結果是,看起來好像也符合觀眾期待。影響可能在後續的放映,陸陸續續會有一些回應,或者說沒有參與過的人,會期待,也想要去參加。
Q:我很喜歡參加音樂祭,但是參加音樂祭有個很大的困擾,就是我沒辦法看到所有的舞台、所有的樂團。想問拍過音樂祭的二位導演是怎樣取捨想要拍的舞台跟樂團?然後怎麼紀錄各角落發生的事情?
Marco Wilms:拍音樂節的時候,我負責拍攝觀眾的部分。我們有個比賽,邀請粉絲投影片,類似自拍的短片。後來發現有個台灣女生拍的影片最吸引人最好看。後來這個女生就變成《Wacken傳奇》紀錄片的主角之一。
施合峰:其實我覺得Marco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活動那兩天是最難拍的。我拍了大概一整年就是那兩天最難拍,因為太多事情同時間在發生,然後也有太多的樂團,所以不可能全部都拍。我就是拍自己喜歡的,因為我的主題不在樂團上,我的重點在蚵仔寮本身,所以樂團變成比較次要。
Marco Wilms:我們在選擇要拍攝對象的時候,有時是樂團自己要去贏得這個機會。他們本身要喜歡上台,喜歡表演。像其中有個羅馬尼亞樂團吸引了我們的注意,所以才拍了他們。
Q:《B級片:地下柏林》裡面有很多片段來自電視或電影,請問裡面有哪些片段是Mark Reeder自己拍的?比如說他走進Nick Cave的臥室,那是他自己拍的畫面嗎?
Mark Reeder:在裡面沒有任何我自己拍攝的影像。那個年代並沒有所謂的自拍,80年代的相機不像現在輕巧,很難拿來自拍,所以都以拍攝別人為主。
Klaus Maeck:不管是電影還是紀錄片,音樂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我擔任電影的音樂顧問,可以拿到2%、3%的電影預算,其實是非常少的,我覺得音樂是很重要的元素,可以改變電影的風格還有樣貌,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應該要爭取50%的預算來做音樂。

Marco Wilm:我在拍攝《Wacken傳奇》時遇到很多音樂版權的問題,音樂版權處理起來是很複雜的。但我仍得想辦法處理,因為音樂很重要,可以加強感受跟情感連結,還可強化畫面和描述故事走向。
David:補充一下,買CD跟音樂版權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說CD是一塊美金,但音樂授權是十萬塊美金的授權,非常非常的貴。
張鐵志:還會再拍跟音樂有關的電影嗎?
施合峰:《蚵仔寮漁村紀事》到《離岸堤》,兩部片的主角都是和家鄉有關,拍完這兩部片後我也準備回自己的家鄉去拍攝紀錄片。
張鐵志:你的家鄉在哪?
施合峰:雲林。我們正進行一個跟空汙有關的行動,希望可以在今年舉行巡迴放映,讓更多人認識空氣汙染的嚴重。
張鐵志:謝謝大家,遊牧影展還有很多很棒的電影,希望大家把握機會觀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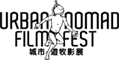

 English
English





